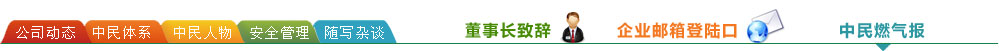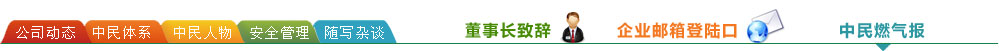莊景云
“五.一”勞動節即將來臨,觸景生情,不由得回想起兒時對勞動的一些趣事。
依稀記得剛到進入幼兒園年齡的我,那時農村還沒有幼兒園,自然無法接受學齡前教育,對勞動的概念也就一無所知,更多的理解都定格在“動”了,認為不用爸爸背、不用媽媽抱、不用哥哥扶就是勞動了,從而也開始身體力行地踐行,在房子里穿廳過巷,在樓梯里爬上爬下,雖然會稍不留神自個摔得臉青鼻腫,但天天下地干活的父母哪有時間顧及這些,仍任由我們繼續“勞動”。
上了小學,勞動的內容也逐步擴大,掃地、洗碗、削馬鈴薯等家務活成了勞動的主要內容,放學前后到田間拔草喂兔子也是接受勞動教育的輔助手段,最苦的莫過于每周單休日(當時尚未實行雙休日)的“勞動改造”了。 父親總是這樣教育我們:“得讓你們多參加體力勞動,知道了干活的苦,才會努力去讀書。”于是,單休日這個本來應該休息的日子卻成了我們最苦的日子,整天跟著父母或哥哥到野外參加真正意義上的勞動。雖然從呀呀學語開始,就受到父母和老師所謂的“勞動最光榮”教育,無奈貪玩是孩子的天性,對勞動缺少的不僅僅是熱情,而是發自心底的畏懼,大有“勞動猛于虎”之感。所以每逢單休日來臨,心里總是暗暗地在祈禱老天爺快點下雨,這樣就不用到野外勞動,可以在家里跟小伙伴們瘋玩一天,真正享受單休日的待遇了。但往往天不遂人愿,在印象當中,單休日下雨的情景總是少之又少,難得一遇。更可恨的是出現過不少夜里下雨、白天放晴的倒霉天氣,在暗自高興一個晚上之后,第二天還得踩著濕滑的小路出去勞動,為此,當時的心情可謂壞到極點,甚至好幾次假裝生病“罷工”,但在父親那威嚴的目光下,含著可憐的淚水,心不甘情不愿地跟在勞動大軍的后面,磨磨蹭蹭地“上工”了。
參加最多的勞動莫過于上山砍柴了。在那一個總不下雨的單休日里,剛吃過早飯,鄰居的伙伴們就相互邀約,組成一支浩浩浩蕩蕩的砍柴隊伍向山里進發。由于年齡尚小,父母還是擔心使用柴刀的安全,砍柴的重任總是由哥哥來完成,而我則承擔起“搬運工”的角色——把哥哥砍好的柴火一根根地收集在一起,再由哥哥用藤一捆一捆地綁好。 此時的太陽已經升起老高,經過大半個上午的勞動,肚子也開始唱起了“空城計”,但伙伴們還是或背或扛帶上一上午的勞動成果,排著長長的一條“線”,在狹窄的山路上一步一個腳印地踏上回家的歸程。途經“風水嶺”這個必經之路時,伙伴們總是停下來休息片刻,美美地對著山泉狂喝一頓,盡情地享受山風帶來的涼快,男孩子們總是十分珍惜這難得的空閑,忘記了饑餓和疲勞,一下子鉆進茂密的林子里玩起了扔松球的游戲,最后在哥哥姐姐們的催促聲中重新踏上回家的路程。 當把柴火扛進廚房的灶前時,正滿頭大汗地忙著做午飯的母親總會不失時機地對我們夸上幾句,一路上翻山越嶺的疲勞頓時煙消云散,從中感到勞動的絲絲快樂。
隨著時間的推移,如今昔日的小伙伴們早已成家立業,為了生活在社會上積極奔走,似乎也繼承了長輩們勞動光榮的優良傳統,真正體會到勞動的意義。
(作者系德化廣安天然氣有限公司員工)